評定書

楊聰賢先生,1952年出生於屏東。1975年東海大學畢業,於1977年赴美學習作曲,1987年獲哲學博士後,曾先後執教於緬因州及新墨西哥州等地。他於1991年返回台灣執教於東吳大學音樂系 (1991-1995) 及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 (1995-2002),目前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,並為台北人室內樂團駐團作曲家 (1994迄今)。
他在大學時期,曾私下追隨史惟亮先生學習作曲,出國之前多次以鋼琴家身份參與賦音室內樂團的新音樂演出與錄音;旅美期間於研究與教學之外並累積了許多演奏及創作的經驗。回台後於教學上投入極多的時間與精神,同時持續不斷的創作;近年來作品在國內及歐、美、亞洲各地區經常被演出。楊教授於1999年1月至3月間接受英國文化協會邀請,前往英國多所大學講學;同時並接受委託為雙子星樂團創作室內樂作品。2002年十二月於台北十方樂集舉行個人作品發表暨座談會,2003年獲頒東元科技獎的人文類獎項。
楊聰賢的音樂是以內斂自省的態度、細緻雕鑿地刻畫自我的生命感懷。其音樂作品中多採非直線式發展,不營造高潮,相反地,以一種模糊、多焦點的美學觀做為創作基礎,這些觀點是他從古典詩詞美學上深刻反思所得。古典詩詞中的象徵、比擬、並置、用典等手法,接軌到後現代文化氛圍,展現了更寬闊的創作視野。
綜觀楊聰賢教授對臺灣文化環境的貢獻,除了勤奮音樂創作與熱心從事音樂教育以外,更積極地從日常生活與學術研究中,體現人文關懷與鄉土認同,經評審委員會審議,評定楊聰賢教授為第三十三屆吳三連獎藝術獎音樂類得獎人。
得獎感言
獲得是一種普世的慾求
失落則為人類情感原型中最為極致者
因為 每一次的失落都是永久的
而大多數的獲得僅為一時
然而 我們卻無時無刻以獲得為念
而一味地迴避失落
唯獨藝術創作者一再地試著透過失落去彰顯獲得的意義
我祈求全能者
讓我經由此次的獲獎
得以深刻地體會到失落的真義
從而更能珍惜所有的獲得
即便只是短暫的擁有
專訪
如果在冬夜、一個歌者-音樂詩人楊聰賢的風格追尋之旅

文/蘇玲瑤
「我想做的,是建立一種風格,但這個風格,不是一再複製自己的某個作品。」2002年,在新作《如果在冬夜、一個歌者…》的發表會上,作曲家楊聰賢如此詮釋自己。
在國內樂壇有音樂詩人之稱,楊聰賢的音樂,冷靜理性中、有著獨特的結構式美學,時常被國內、以及歐美、亞洲等地區的音樂會選為演奏曲,作曲對他來說,不只是音符的組合,而是感受的抒發。
創作的路上,楊聰賢喜歡從文學裡找靈感,他花很多時間在閱讀,但讀最多的、卻不是音樂類的書,而是當代文學作品。他認為音樂類的書太過於技術層面,但技術卻非音樂最本質的東西,在日本文學中、他找到了當代性,不背離東方特質、卻又同時兼具西方關注的議題,1994年完成的《川端康成禮讚》,就是從日本文學中,焠鍊出的作品,是和作家的對話、也是致敬。
楊聰賢在東海大學史主修鋼琴的那段歲月,正逢許常惠與史惟亮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進入尾期,第一次上史惟亮的曲式學,就受到相當大的震撼,他體會到史惟亮和其他教樂器老師的不同,毅然而然跑去要史惟亮收他為學生,雖然後來未能如願,但暑假期間跟著史惟亮、賴德和四處去原住民部落採集音樂的經驗,卻對他後來作曲生涯有莫大影響,只不過這份影響,一醞釀、就是十多年。
東海畢業後,楊聰賢一心只想了解國外音樂上最新的思考議題和關心面向,於是,他收拾行囊遠赴美國求學,1977年到1987年,花了十年時間、從碩士唸到博士,並且相繼在緬因州的鮑登學院(Bowdoin College)、以及新墨西哥州的聯合世界學院任教、擔任音樂系的系主任,在當時、他是第一位在美國大學教音樂的台灣人。
1991年返國後,楊聰賢先是在東吳任教,後來相繼轉往交大、以及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擔任專任教授,教學之餘、潛心在作曲上,是國內少數的高產量作曲家之一,回國初期就陸續發表了《那些漂泊的年月》(1992)、《琴樂》(1993)、以及《山水寮札記》(1994)等作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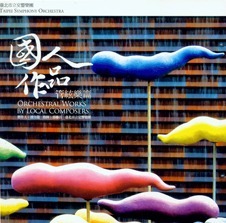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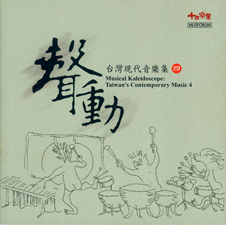
楊聰賢作品
由於長年在國外求學與任教,整個80年代、台灣社會歷經解嚴前後的劇烈震盪,對楊聰賢來說卻是段空白。或許是為了彌補這段心中的缺憾,回國後的楊聰賢,時常帶著學生,參加街頭運動,廢除刑法一百條、廢除萬年國大,只要是訴求民主改革的活動,他都積極參與,1996年完成的《佚名之島1995》,就是為台灣而做,他以傳統樂器作為主旋律,搭配上西方打擊樂器,兩種截然不同音色的東西方樂器一起演奏,時而互斥、時而卻又巧妙融合,就像是在尋找一個共同存在的平衡點,而這、正是長期接受西方樂理技巧洗禮的楊聰賢,內心意圖回看自身文化的寫照。
爾後,大學時代潛伏了幾十年的民歌採集的基礎,也開始浮現在他的作品中。2007年完成的合唱曲、《三首魯凱情歌》,就是過往經驗的凝結。回到台灣後,楊聰賢不只教書、作曲,也和國內樂團合作,他長期為台北人室內樂團、十方樂集寫曲,也因此見證到國內小型樂團發展不易、經費擷倨的窘境,他感嘆古典樂在台灣的小眾、也氣憤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好大喜功、不切實際。
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,是一個沒有風格的年代,追尋著個人風格的楊聰賢,在音樂上找到了自己的風格沒有?這個問題、沒有答案,要一探究竟,唯一的方式,就是去聆聽他的作品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