評定書

詩人鴻鴻先生,本名閻鴻亞,1964年出生於台南。年少之時即才華洋溢,1990年3月出版第一冊詩集〈黑暗中的音樂 1982—1989〉,詩藝不凡,爾後創作不懈、源源不絕,未曾間斷,以編年式持續出版一冊一冊質量俱足的詩集,分別是〈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的旅行 1990—1995〉、〈與我無關的東西 1996—2002〉、〈土製炸彈 2002—2006〉、〈女孩馬力與壁拔少年 2007—2009〉、及最新詩集〈仁愛路犁田 2009—2012〉,詩作成果十分豐碩可觀。
鴻鴻先生每個階段的詩作,既延續自由而率性的風格,更不斷擴大關懷層面,特別是對弱小國家、弱勢民族,橫遭國際強權侵略、壓迫、欺凌的處境,有一股忍抑不住的正義之氣,予以撻伐。近十幾年來,一面關心國際社會,同時深情注視賴以安身立命的台灣島嶼廣大土地,無論是批判不當的文化政策,或為維護環境正義、為農民請命,不只發而為詩為文,更公開站出來,走上街頭講台,充分展現將理念付諸實踐的行動力。
詩作成果、社會參與之外,鴻鴻先生亦是傑出的電影和劇場導演,藝術活動多元,策展台北詩歌節,並創辦〈衛生紙十〉詩季刊,集結多位年輕新銳,推動同時代的詩藝,隱隱然形成一種新世紀的新格調,將日常口語化的語言,運用得十分自然流暢,貼近生活的現實感。爰經評審委員會審議,評定鴻鴻先生為第三十六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得獎人。
我在台南出生,因此得到由這位同鄉的民主先驅設立的獎項,特別感到溫暖。然而,忝列過往眾多得獎的前輩典範之後,得到這個獎也讓我倍感惶恐。我發現基金會對於這個獎項的簡介,有兩個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說法:一個是「『吳三連獎』屬於『終身成就獎』,另一個則是「有繼續創造潛力」。我投身寫作雖逾三十年,但近十年才真正找到自己與這塊土地的關聯,在創作的道路上重新出發,資歷實在不長,談「終身成就」,未免太早。我寧願相信,評審委員是看在「有繼續創造潛力」這一項標準,而頒獎給我這個仍在摸索的創作者。

文學和社會環境無法脫鉤。解嚴之後,台灣文學進入一個新的時代。過往處理政治議題必須小心翼翼,用象徵、比喻、甚至超現實的想像來轉換,現在進入了一個可以用文字直接表達立場與關懷的時代。詩不必躲在語言歧義之後,變成隱諱的猜謎遊戲。在明確的觀點與藝術的操作之間,可以不再是此消彼長的取捨關係。但如何用曉暢的語言、巧妙的切入角度,傳達毫不迴避的態度,甚至號召讀者起而行動,成為詩人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同時,前輩吳晟、柯一正、小野等不斷號召我們上街頭爭取社會正義、文化改革,他們的精神與良知成為指引新一代創作的明燈,我也要在此特別申謝。
專訪
書寫街頭的資深文青,鴻鴻用詩、為社運留下記錄

文/蘇玲瑤
出過十多本詩集、散文與小說,台灣現代詩青壯派代表之一,同時也是台灣劇場、電影、紀錄片的知名導演、策展人,但最近幾年、"鴻鴻"這個名字之所以頻頻躍上媒體,卻是因為在不同社會議題的抗爭場合裡,都可以看到他那為求公義、振臂疾呼的身影。
「我的寫作是一種街頭書寫,也是社運現場的記錄。」
幾乎每個周五晚上,鴻鴻都會背著招牌帆布包,出現在自由廣場「反核四五六」人群中,闡述理念、也進行他所謂的街頭書寫。
本名嚴鴻亞的鴻鴻,從小跟著爺爺念唐詩、國中時期受老師啟蒙開始寫現代詩,對他來說,詩、已然是生命的記錄,也是情感的凝結。鴻鴻早期的詩,圍繞在抒情氣氛上,流露出一股、被詩人吳晟形容為「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」,曾經獲得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、聯合文學獎新詩首獎、南瀛文學傑出獎等諸多獎項,27歲時,還參加編寫導演楊德昌的電影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」劇本,拿下了金馬獎。寫作上的才華備受肯定,但2000年後,這位什麼都想嘗試一下的「文青」,風格卻開始轉向。他開始關注樂生保留運動,近年來更積極參與國光石化、中科搶水、以及反核、反服貿協定等社會議題。投入社運,讓鴻鴻對詩的現代性、有了不同的思索。
「台灣解嚴之前,創作都是採用一種比較迂迴和超現實的方式進行,但解嚴之後,尺度開放,大家可以無所顧忌地寫,但這時文學反而遇到一個瓶頸、一個更大的挑戰,就是當你什麼都能寫的時候,它的文學性從何而來?」
從「土製炸彈」到「女孩馬力與壁拔少年」、再到「仁愛路犁田」,晚近鴻鴻出的詩集,都緊貼著社會現實。親身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,鴻鴻了解到社會結構與權力脈絡,在街頭抗爭上遇到的人、聽到的故事、吸收到的觀點,都轉化了他對社會的認知,也自然而然融入詩作中。他一改過去文學家評論時事的詩作、那種既間接又迂迴的方式,而是採用直接面對的態度,以時而幽默、時而魔幻寫實的口吻,去探討、嘲諷荒謬的國家機器。
「我覺得詩可以為自己或這個時代,留下記錄,它不應該只是一種個人心情的發抒而已。」
鴻鴻自言從社運中,得到相當多的養分和創作靈感。雖然也導戲、拍電影、寫小說,但他認為這些創作實行起來都曠日廢時,有時還得傷腦金籌措資金、或是得和合作團隊進行繁複的溝通,但詩卻是最快、最直接、也是最純粹可以抒發己見的文體,只要想法成熟,一個晚上就可以寫下來,第二天就帶上街頭去念,而這樣的作品,一方面表達出意念、一方面也因詩特有的文學性,讓讀者很快就能掌握到要傳遞的訊息。
「農民上街頭吶喊、歌手上街頭唱歌,而我只會寫詩,所以就帶筆上街頭。」
寫了很多反核四、反中科搶水的詩,為這些社運留下見證,鴻鴻也讓自已的讀者,從紙面上的讀者,擴充到街頭上活生生的人,即時的反應,很快就讓他明白一首詩的成功或失敗,而這類街頭書寫的抗爭文體,也正是台灣文學所欠缺的傳統。他認為在漢人既有的文學傳統裡,真正有才智的詩人,都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,要不就把作品轉化、透過寓言方式來發表,但國外詩人卻給了鴻鴻很大的鼓舞,像作品廣被翻譯的以色列詩人耶胡達‧阿米亥,還有阿拉伯世界知名詩人、巴勒斯坦的穆罕默德‧達維希等,詩作再再都反應出社會現實。
「西方文學傳統裡,詩人有著一種為民喉舌的位子,這種直接面對的文學,卻仍然可以擁有高度的文學性,情感非常真摯動人,讓我理解到,原來現實書寫可以這麼強大,可以直接去面對世界。」
帶著這樣一份使命感,鴻鴻選擇與街頭群眾站在一塊,他堅信創作者唯有寫自己最關心的議題,才會寫出好作品,而這樣的作品,也才足以映照出他個人的時代。
鴻鴻高中時曾在雲門舞集習舞,還加入路寒袖創立的「漢廣詩社」寫詩,大學考上當時甫成立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,畢業後曾擔任電影記者、雜誌主編,而現今則擁有劇場電影導演、作家、策展人、講師等多重身分,充滿創造力、而又熟悉跨領域的背景,讓他在2004年接手策劃台北詩歌節之後,便努力把詩,與劇場、舞蹈、表演等結合,注入更多元的美學觀,他邀請伊拉克、伊朗、西班牙等國家的詩人來台進行交流,讓詩作的呈現,變得活潑又具親和力,還因此吸引出一批喜歡詩的新文青。
「詩的風格會隨著時代改變,自然而然會找到它新一代的讀者,所以我不覺得詩會變得邊緣,因為它本來就在邊緣。」
不只辦詩歌活動,鴻鴻還辦詩刊,提供年輕人發表評台,要讓詩成為可以抒情、還可以分析、言志、觀察、甚至是疾呼的工具。在講究輕薄短小的數位時代,他認為詩作為一種簡潔有力的文體,反而成為一種容易被接受的媒介,現在的他,常詩一寫完,就立刻PO上臉書,來了解網友對詩的回應。
「進入新時代,詩不必躲在語言的後面、變成猜謎遊戲,但在明確的觀點跟藝術操作之間,如何取得一個平衡,反而成了新的挑戰,身為詩的創作者,我坦然面對!」
除了寫詩、寫劇本,鴻鴻也持續導戲、策展,他的「黑眼睛跨劇團」,年底還將推出兩年來最大的創作計畫,一個舞台輪流上演兩齣戲、充滿實驗風格的「換屋計畫」,也將開拍楊儒門的紀錄片,而可以肯定的是,這位創作上的過動兒,未來也將繼續透過他那自由而率性的詩句,來發出正義之聲、關注社運的脈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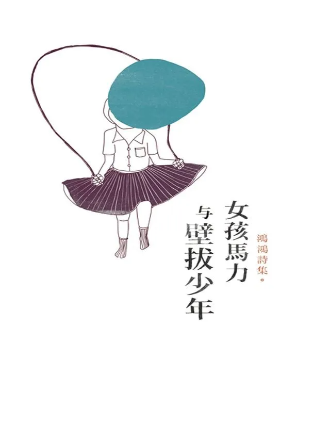
鴻鴻,《女孩馬力与壁拔少年 》(台北:黑眼睛文化,2009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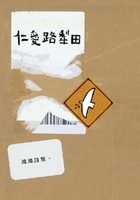
鴻鴻,《土製炸彈 》(台北:黑眼睛文化,2006)

鴻鴻,《鴻鴻詩精選集 》(新北: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,2010)

